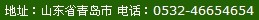|
南昌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http://pf.39.net/bdfyy/bdfyc/150505/4618891.html 旷远的忧伤 刘晓露 诗经·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看那黍子一行行,高粱苗儿也在长。迈着步子走且停,心里只有忧和伤。知我者说我心忧,不知者说我有求。高高在上苍天啊,何人害我离家走!看那黍子一行行,高粱穗儿也在长。迈着步子走且停,如同喝醉酒一样。知我者说我心忧,不知者说我有求。高高在上苍天啊,何人害我离家走!看那黍子一行行,高粱穗儿红堂堂。迈着步子走且停,心内如噎一般痛。知我者说我心忧,不知者说我有求。高高在上苍天啊,何人害我离家走!全诗共三章,三章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复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正是受了《黍离》的启发而写。不仅仅是陈子昂,后世许多文人写咏史怀古诗,也往往沿袭《王风·黍离》这首诗的音调。从曹植的《情诗》到向秀的《思旧赋》,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无不体现着《王风·黍离》的兴象风神。而“黍离”一词也成了历代文人感叹亡国、触景生情时常用的典故。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评价该诗时说:“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此专以描摹虚神擅长,凭吊诗中绝唱也。”旷远的忧伤刘晓露那天,我站在晋南小城襄汾附近的陶寺遗址,仰望矗立于此的古观象台复制模型。观象台的背后是塔儿山,阳光从那里倾洒而来,在石柱的缝隙间穿过,地上阴影斑驳。而远处,是一望无垠的麦田,绿油油的麦穗正在拔节;麦芒尖尖的,像针,像箭镞,向头顶的方向刺去。多年前的观象台,欣欣向荣的植物,蓝得晃眼的天,一朵游荡的雪白的云……初夏的原野阒然无声,辽远而寂寥。古老的土地上,到底发生过什么?“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当这样的诗句浮现在脑海,当麦变成黍和稷,我想,《黍离》的主人公该出场了。千年之前,沧桑的去国者曾经在这样的天地间行走。谷物疯长,狂野的生命力无法遏制,风中它们一排排倒下又一排排倔强地挺直身躯。眼前的景物如此蓬勃,可他的忧伤却如海水漫溢。这个心事重重的男人步履缓慢,内心郁结,长发散乱,紧皱的眉头和暗淡的眸子泄露了内心的苦痛。他是在思念故国吗?国破山河在,草木不知愁。曾经的华屋广厦如今已成断壁残垣,只能在梦中依稀再现。他是在想念故人吗?亲人、朋友、同僚,都已不知流落何方,殊不知转身便是永别,此刻他孤零一人在异乡流浪。他是在回首往事吗?那钟鸣鼎食的时节,朝廷上,他向君王进谏,意气铮铮,散了朝,未及在府前下马,贤惠的妻子早已笑意盈盈迎了出来,而一双可爱的儿女张开双臂飞奔着扑来……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忧心忡忡到底为何?但我们知道,曾经的锦绣繁华,风流云散,俱往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的心是幽深的空谷,在那遥远的地方遗世独立。有人懂,有人不懂,而更多的是不懂吧。不懂,多么让人怅然;不懂,才渴望懂。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发出了这样的慨叹。短短两句,撼人心魄。太多坚硬或柔软的心被猛然击中,在刹那的失神中,狠狠痛起来。忧伤那般浓烈,悲愤那般刻骨。叹息之后,内心喷涌的情感再也无法克制,这个踽踽独行的男人禁不住仰天发问:“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声呐喊,和着血和泪,道出人生无尽的痛楚和无奈。之后,我仿佛看到那个清瘦的背影颓然远去,隐蔽于草木离离间,消失在历史深深处。黍离之悲,因之成为流传至今的固定词语,表达着悲悼故国、物是人非的伤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典故。我们看到:屈原,汨罗江畔长久徘徊;陈子昂,幽州台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们有着同样的姿态,用诗歌传递着同样的情怀。读《黍离》,读历史的暗流涌动,读旷远的忧伤,读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诗意表达。(本文刊发于年4月)作者简介 刘晓露,山西教育出版社文史读物策划室主任。编辑出版“名家作品中学生典藏版”系列以及《云南上座部佛教史》《中国分体文学学史》等图书。长按
|
当前位置: 汨罗市 >读诗经诗经middot王风mi
时间:2022/5/2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深圳装饰设计公司电话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