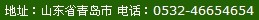|
儿童白癜风如何治疗 http://pf.39.net/bdfyy/tslf/ 哇塞!快来围观!首届汨罗江文学奖10万元大奖散文长这样~ 此次汨罗江文学奖中,来自秭归的作者周凌云的《为屈原守灵》获散文类离骚奖,快来看看全文吧!为屈原守灵 文/周凌云 屈原庙里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屈原,另一个是徐正端。徐正端守庙。屈原,挺立在大堂之上。徐正端,住在大堂之下右侧的一间小厢房里。小厢房一面的窗户开向东方,伏虎山全景和太阳的温暖都可以投射进来,雨飘不进来,寒风吹不进来。 今年春天我见到的徐正端,已经八十六了,精神气韵不如往年。走路蹒跚,说话气喘,眼睛暗淡无光,脸上的老年斑又添了三块。高血压、糖尿病严重了。我在庙里见到他时,医院,脸上没有恢复元气,灰黄色,像干枯的柚子壳儿。我暗暗替他担心,希望他能打过九十岁。八十四岁时,我带了几个诗人到庙里为他祝寿,献上我们颂扬的诗作,他满心欢喜,人生终于渡过了八十四这个大关啊。这是一个人敏感的关口。“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乡亲们是这样说的。我观察过一些老人,这个年岁都焦虑不安,生怕被阎王接去了。平时都说不怕死,但当死挨近自己的时候,恐惧来了。那一年,徐正端住过多次院,身体一有风吹草动,医院,他还想多守几年庙。九十岁,但愿我还来为他祝寿,应当会有那一天。几年的光景一眨眼也就会过去,只要他能挺一挺。他眼上的眉毛还是那样坚挺,钢针一般,一寸来长,黑黑的,这是长寿眉。眉毛是不是和身体的状况没有多大关系?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他的一切都在变化,越来越大,只是那眉毛一直那样直直的,像剑,能遮太阳,能挡风雨,一只鸟儿落在上面也不会弯曲。 从眉毛看性格。徐正端说话刚直,不转弯,不藏着掖着。今年看起来说话底气不足,以前看到的徐正端说话响亮,像敲钟声。看不惯的事,总要说,也要管一管,嘴像只大喇叭。辩论问难,是一把好手。其实,都毫无用处,一个守庙的人,一个写诗的人,有什么力量?屈原位高权重,尚且不能影响一个人,只能满怀忧伤,四处流浪,他一个守庙的老朽,又能影响谁。只是路见不平,发发牢骚而已。刚直的性格,让他吃了大亏。这和屈原一样。他原本在新滩南岸的一个学校教书,因仰慕屈原曾去九畹溪办过学堂育过人才,遂要求调到九畹溪小学去教书。追寻屈原的足迹,种兰育蕙,亦步亦趋。一九五八年,天下烟雾朦胧,在一个把右派指标分到单位的年月,因说话耿直,遭遇厄运。子虚乌有,栽赃陷害。壮年之躯也承载了严重的罪过。报复他的人说:不送你上丰都做个死鬼,也得送你到沙洋牢改。从此,徐正端走上了二十一年的牢狱生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人生宝贵的年华,就这样丢去了一大截。拨乱反正,出狱,教了几年书,退休了。退休后他就直接搬进屈原庙。他觉得自己和屈原是命运共同体。迫害。流浪。过着非人的生活。写诗。写心中的不平。 他支了一张铺,立了一个灶,带了一柜子书,安安静静住下来。 住进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冷清、空洞的屈原庙活泛起来,呆板的屈原塑像生动起来,庙堂内外空灵起来。庙门开关的声响传到村头了,鸡叫一样嘹亮。炊烟袅袅绕绕地浮起来了,像是插在庙宇上的旗幡。脚步在每个角落踏动,铿铿锵锵,也惊醒了一系列的细小生命。还有了书卷气,墨香盈室、吟诵不断。一个人物的活动是能带动一切的。庙外也进入了四季的正轨,花草该枯时枯,该荣时荣,树木该零落时零落,该繁茂时繁茂。有人能看管这些花红柳绿,收拾残枝败叶,是不一样的。人给这些生命带来更加旺盛的活力。 徐正端住在庙里,也陪伴屈原的孤寂,守护伟大的诗魂。每天早晨当草莓汁一样的太阳从窗格子里钻进来的时候,起床擦一把脸,走进天井,数一阵空中飘浮的浪漫彩云,然后打开大厅的门锁,开始为洁白的屈原除尘。本来屈原是傲世独立、洁白无瑕的诗人,是无需除尘的,但因为世俗的尘埃总是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所以徐正端老人便将为屈原除尘、保持洁白的躯体定为每天最主要的功课,他要让这位伟大的诗人放射出永久的、洁白的光芒,让游人瞻仰。 除尘之前,他在诗人的面前,虔诚地点燃一炷香,让这炷香梦幻般悠悠地袅起一缕一缕的诗意之后,便轻拂慢抹,用温暖的孝心擦拭屈原皮肤上的微尘。诗祖啊,这时你的感觉是不是洁白的雪在飘落?是不是有一些细得不能再细的太阳刷在你的身上? 静静地为屈原除尘,默默地在大师面前诵吟《离骚》,这是徐正端最幸福的时刻。徐正端已离不开屈原庙,离不开屈原。这样的幸福时刻他要天天拥有。 除了为屈原除尘,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比如打扫庙宇。他把庙内庙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要把生活中的一些世俗的事情扫到一边,腾出干净的地方让宾客坐下。 比如培植橘树。屈原不是写过一首诗叫《橘颂》吗?颂家乡的橘呢!不能对橘树马虎,要用尽心思去剪枝、去施肥、去呵护它累累的果实,让橘树的根深深扎进诗的沃土。他还要去培植兰草兰花,这是屈原最心仪的花草,他也很疼爱,要浇水要去杂草,还要把屈原写兰草的诗句背一背。 比如联络骚坛诗友。想念哪位诗友了,就写一首七律或绝句或骚体诗,表达想念之情,送给友人。诗友的和诗,耐心玩味,珍藏起来,用毛笔又誊写一遍,编入诗丛。屈原庙是骚坛的笔会中心,他则是骚坛诗友的轴心,一切联络都自老人始,也自老人终。 他也接待三三两两的游客,殷勤讲述屈原的诗篇和事迹。曾经来了一位博士,和徐老谈论“屈原否定论”,一时徐正端勃然变色,屈原就出生在我们村里啊,怎么可以否定?博士没想到徐正端反应是这样激烈,竟然义愤填膺,顿时噤若寒蝉,再不理论。徐正端是屈原庙里的守护神,是屈原最忠诚的卫士,他不能让任何人否定屈原。 他还着手默默做了一件事情。花掉了多年的积蓄。先花几个月的光阴,用楷书将屈原的二十五首诗书写下来,然后请人在外县拖回一车石料,用半年的时间请匠人们铭刻,打成一块块石碑,将诗碑镶嵌在屈原庙的大堂,还买回一块块大玻璃将这些碑罩住,让诗碑永远陪伴着诗人。诗碑环绕着屈原塑像,就像忠实的守护者。屈原低头沉吟,迎风徐步。这些碑林就像书简,屈原可以一一翻开。千古诗篇焕发出光辉。屈原庙顿时变得阔大而充盈起来。徐正端完成了这桩大事,感觉像完成了整个人生。每次我走进这座庙,都要在诗碑前踱来踱去,透过玻璃,诵读屈原的诗句,屈原的忧愤、高洁感染着我,徐正端的义举也感动着我。实际上,徐正端把钱看得重,儿子曾向他借钱,没过几天,就要了回来。把钱用在想用的地方,才对。钱花在庙里,不心疼,借出去,不放心。 徐正端永远不忘一年中的两个日期,一是正月初七屈原的生日,再就是五月初五屈原的忌日。正月初七,徐正端总要买来一挂鞭炮,在庙里放上一阵子,在屈原的生日里与屈原共度良宵。屈原的生日,乐平里的人记得,他记得。五月初五端午节,是屈原投江殉难的日子,同时也是乐平里泥巴腿子诗人们到庙里聚会吟诗的日子。这一天,徐正端要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准备茶饮和酒馔,以迎迓他的诗友们。他看到敞着衣衫、卷着裤管,大口大口吧咂旱烟的诗友们陆陆续续从毛狗子道上走来的时候,就兴奋不已。这种兴奋并不是因为他和这些诗友曾在一起耙过田、栽过橘、砍过柴禾,而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写诗这一特殊的志趣,是“诗”把他和这些农民兄弟紧紧粘在一起。诗会结束后,徐正端就把骚坛诗友们的诗留下来,用毛笔楷书仔细誊写,然后装订成册。这些诗集,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凝聚了他的心血。 徐正端自己也写诗。写骚体。 时维五月兮,节届端阳。 蒲艾高悬兮,驱邪迎祥。 楚天默哀兮,素冠素裳。 竞渡龙舟兮,吊古忠良。 争投角黍兮,遍撒江湘。 饫餐水簇兮,圣体勿伤。 年年此日兮,大地茫茫。 骚人墨客兮,萃聚一堂。 笔呼墨号兮,洒洒篇章。 追溯高节兮,爱国之光。 孤忠夙愿兮,美政兴邦。 今世今朝兮,祈公鉴赏。 在庙里读诗与写诗都是非常冷清的事,尤其是冬天,雪降落到诗人的生活中,诗人就一直在倾听落雪的声音,偶尔远眺一番被雪覆盖的村庄和田野,便又回到暗淡无光的炉边。在炉上烤几个红薯和土豆,黑凳上放上一小碟腌菜和一小碟花生,便悠然喝酒。喝酒时除琢磨一两句诗外,也想一些人和一些事。想得深远的时候,眼角冷不丁也落下一两滴浊泪来,是不是谭光沛、杜青山两位诗友逝去的身影又在他心里翻滚了?是不是骚坛将面临后继无人的景况令他忧郁? 他是有些忧郁了。仅仅把个庙门守住有什么用啊?他要守住的是屈原的灵,是屈原的魂。要将屈原的思想在乐平里传下去。自己已至耄耋,将要入土,还能守几年庙呢?写诗还能写几年呢?灵气已经飞逝,才思也已枯竭,说乌呼哀哉,就是一口气的事儿,眨一下眼睛的事儿。但是屈原的诗作要传下去啊,继承屈子遗风的骚坛要传下去啊!这是大事,不能马虎。要传下去,得靠后人,当务之急,是要拉携几个青年娃子,传递骚坛的香火。 寻寻觅觅。找寻能读会写的好苗子。这是火烧眉毛的事儿。只要是棵苗子,徐老就会去精心地呵护、浇灌、亲近,教他读屈原读楚辞,教他写骚体诗、格律诗。但是现实让他沮丧。一个女孩子,写诗填词已入门,也能在端午诗会上登台亮相了,却走了。几个后生,徐老手把手地教,都有了长进,写出的诗像模像样了,但也难耐写诗的寂寞和生活的贫困,鸟儿一样扑楞楞飞了。这让徐正端极度的落寞和沮丧。心血白费了!要教一个人由不能读懂《离骚》,到能读会背,由不能写诗到会写,由平平仄仄到上下去入,不知要费多少口舌,耗多少脑筋,熬多少夜。煮熟的鸭子飞了,他的心多痛啊!当然,他也明白,农民最需要的还是糊一口嘴!穿一身衣,需要的还不是写诗,也不是研究屈原。如果他们关心屈原的话,不是关心屈原的本身,也不是屈原的“求索精神”。“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精神世界离他们还是很远的。他们琢磨的,是屈原故里的旅游会不会火热,乐平里的大规模开发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说屈原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实在的东西。如果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青年人还是会走的,会毫不犹豫地丢下楚辞和写的诗稿,会撇下徐老头子。诗毕竟换不来粮食,更不能鼓起腰包。这些和徐正端的想法相去甚远。 徐正端,心仍然不死。他去叩小学和中学的门了,找校长商量在学校开办“楚辞课”,在老师中结交诗友,在学生里找好苗苗,这是他残存的希望。校长和老师们也还是热情的,也经常请他去讲楚辞讲屈原,也乐意让学生到庙里去听一听、看一看。这让徐正端宽心,打心窝子里高兴。后来,学校对开办“楚辞课”也渐渐冷了,停了。因为楚辞课不能给学校带来教学成绩,也不能给学生带来中考分数,学校得围绕考试的指挥棒转,不转不行,不转学生就得吃亏,误了学生的前程,谁担得了责任?徐老又茫然了。如果不找几棵好苗子,骚坛将会倾覆,诗也将是一片废弃的旷地,再也不是一片绿洲了。徐正端是真正在忧虑骚坛的事了。 徐正端在离屈原庙几十步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还买来一些长条板凳,办起了“离骚径院”,讲屈原的作品、屈原的故事,讲三闾八景的传说,也讲骚坛的精神。“离骚径院”是极其简陋的,不像讲课的地方,但他讲这些东西却是滔滔不绝。有时学生来听,有时游客来听。只要有人来听,徐正端就来劲、兴奋,口若悬河。他找到了寄托。“离骚径院”热闹了一阵子,又冷冷清清了。好长时间没有人光临。不过这种景况老徐早就预料到了。 是把“离骚径院”的门关上还是一直就这样开着呢?徐正端有些犹豫。 小孙子开始读小学的时候,徐正端就牵着他的手常在田畦上遛达,给他讲屈原小时候的故事,背屈原的诗给他听,也常把他留在庙里做伴儿。他对小孙子说:“上不了大学就在村子里待着啊!”现在徐正端又有了重孙子,也快上小学了,他又在向重孙子背屈原的诗了,讲屈原的故事了。 每天关庙门的时候,徐正端总要坐在高高的门坎上看一阵日落,直到另一边升一个弯月。他想:“我死了以后,谁来守庙呢?我的孙子会来吗?重孙子会来吗?” 这个春天,气候适宜,我想在庙里住一个晚上,徐正端爽朗答应了。徐正端没有拒绝过住庙的人,还给我讲了些感人的故事。村子没有虫声没有鸟语,一片死寂,屈原庙里只有我和徐正端偶尔低语。如果咳嗽一声,全村也许会有一点颤动。这样的寂静令人害怕。徐正端说,在他前面守庙的一个人,住了三晚,说庙里闹鬼,跑了。他住进来第一个晚上,听到天井里有撒土的声音、落石的声音,也紧张,但是还镇静。坚信庙里只有屈原的灵魂,不会有鬼。自己的眉毛长,火焰高,是鬼他也看不见。只有鬼站在他面前,他才会相信有鬼。陷害屈原的小人才是鬼呢。是鬼,徐正端坚挺眉毛的万丈火焰,也要把它压下去。远方一位朋友曾向我说,她曾看见过鬼,是她小时常见的一位老者,死去多年了,同时几个人在路上走,别人没看见,她看见了。我感到纳闷,她是不会说谎的。鬼真的存在吗,人死了,影子还在吗,灵魂还在吗。我说:肯定是幻觉。鬼,是在心里的,心里有鬼,胆小,它就会冒出来。徐正端不怕,让鬼撒土吧,投石吧,只要不在他眼前晃动,他就不相信。如果屈原再现了,他倒会欣喜若狂。看看真实的屈原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传说中高大魁梧的美男子。几十年过去了,天天住在庙里,屈原一直没有出现过,可见人死后,是不可再现的。只有他的诗是魂。我佩服徐正端的胆量和勇气,如果我来守庙,纵然不相信有鬼,也害怕。 徐正端一直睡着木板铺,两块木板拼凑,外面罩着蚊帐,一年四季罩着。他脊椎有毛病,不睡软铺,这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内疚。好多年前,和他也是在这间厢房里聊屈原聊骚坛,不觉已到深夜,我要去三闾饭庄住宿,他坚持要送我下山,就在要通过屈平河时,他从一道坎上跌了下去,腰不能伸展,脊柱也不能动了,痛得厉害。我傻眼了,不知如何是好。陪同我的骚坛社长黄琼立即背着他向村卫生室奔去。我的心一直悬着,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他呢。医院拍片,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跌跤把这些毛病引发出来了。徐正端在木板上睡了一个多月,才出院。医疗费我出,他不干。他说:摔跟头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大意。他回庙里后,就一直睡木板床。 静夜里,在并不明亮的灯下,我读着《骚坛联吟集》,这是他与李国杰、李盛良、郝大树四人合出的诗集,印刷的,又翻看着他正在整理的两部诗集,宣纸装订,毛笔誊写,一丝不苟。这应当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许是最后的作品。他在庙里待了近半个“甲子”,和屈原共度了几十年光阴,写了这两本集子,知足了,后半生完美了。他一直在精神的高地快活着,悠闲自在,这是他人生最充实、自由的时光。我很想知道,这两本诗集,如不出版、发表,将会传给谁,我不希望它散失,或当引火纸烧掉。不论写得好,写得歹,都是珍贵的,这是守庙人的心灵记录。如果他交给我,我会整成档案,传下去。但是我没有说出口。他自己会做出决定的。两部诗集,存在与丢失,对任何人都毫无影响,但是他却看得极为重要。其实不用愁,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会交出来的。晚上他只是对我说,骚坛诗会上诗人们吟唱南腔北调,调子偏远了,要纠正过来,回到正统,把古音传承下来。人,物色好了,就选明月。明月聪明,脑子活络,有好基础,能传下去的。我也同意,明月是棵好苗子。诗写得好,山歌调子唱得鲜鲜的,嗓子清清亮亮,比鸟儿还脆,还婉转得多。又是个热心人。 我心里激楞一下,感觉徐老在交待后事一样。他洞察了我住庙的目的了吗?我后悔住下了,我不能让他感到生命渺茫,只能让他看得更远,还希望他活过百年,一直守庙。其实他把一切后事都安排好了,自己的穴地挖好了,墓碑也树起来了。是块好地。徐正端自己看的风水。这块地只有几厘,他用六分田粜来的。正式粜的那天,双方签合同、签字,请来村干部见证,生怕对方反悔。几厘田粜来六分,哪有不干的?这是划得来的买卖。当徐正端把碑树起来的时候,别人才明白,喔,是块宝地,宝地是难寻找的,宝地,自己竟然不知,但木已成舟,无可奈何,还说什么呢,让“老和尚”骗了一把。村里蛮多人把徐正端叫“老和尚”的,守庙的人就是和尚嘛。十年前,徐正端就在打这块地的主意呢。很如意。这块地,就像下山龟,龟头伸展,翘望远方。龟,是长寿符号。对面是蛇山,蛇,也是蜿蜿蜒蜒,向龟梭来。龟传子孙,靠蛇交配。这龟蛇二山,在此相会,不是好地是什么。徐正端学《周易》,会看地,自己的墓穴,当然最上心了。自己的后代,发不发人,发不发财,这穴地重要着呢。风水好,人丁旺呢。 早上醒来,庙外小雨靡靡,征得徐正端同意,一同去看他墓地。墓地在一片包谷地里,在一条溪沟之畔。徐正端说的龟形地,看起来真还有那么一点形态。墓联:百炼千锤能固我,三回九转耐磨人。这是他自己写的,这两句就像两杯浓浓的果汁,酸酸甜甜,是高度压缩的一生。平淡吗?教书,坐牢,守庙,也平淡。曲折吗,教书,坐牢,守庙,也曲折。他的一生就在这两句中活着。短暂,一眨眼功夫,一轮太阳就这样翻过山了。一生,总体上也是难熬的,天天和时间磨,和世态较劲儿,风来雨往,也盼不出个日头来。哎,有块好地,就有个好归宿了。徐正端瞧着自己找的地,树的碑,自己写的墓联和碑文,特别满意。我看到他的表情是得意的,有几分儿童般的快活。 首届汨罗江文学奖现代诗的10万元大奖作者身份已于日前揭晓,那么,散文类10万元大奖作者又是谁呢?身份会不会同样让人意外?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揭开谜底: 散文离骚奖(一等奖)获得者周凌云:他从秭归来秭归与汨罗,一个是屈原出生地,一个是屈原灵魂地,一个始点,一个终点,它们构成了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高地,也贯穿着血脉相连的真切情感。 这名从秭归而来的作者,出生于年,曾从事过教师、新闻记者职业,现从事文艺工作。他一生热爱文字,从年起,在文学刊物《长江文艺》《芳草》《散文百家》《飞天》《文艺报》《草原》《散文诗世界》《创世纪》(台湾诗刊)等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也在《光明日报》等几十家报纸副刊发表作品。 文字来源于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miluozx.com/mlsxw/8181.html |
当前位置: 汨罗市 >哇塞快来围观首届汨罗江文学奖10万元
时间:2021/6/2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洪水蓝色预警刚刚,岳阳水文中心又传来最
- 下一篇文章: 作文ldquo凤头rdquol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