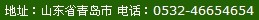|
汨罗江畔 一般的人,出了地级市又没出省,向外地人介绍自己老家时,通常都会说“我是邵阳人”或者“我是常德人”之类。再问细了,才会说“我是邵阳绥宁的”或者“我是常德安乡的”。但我是个例外。有人问我老家是哪里,我通常都说:“汨罗”。我自己觉得汨罗很有名了,但仍旧有人不知道:“汨罗是哪里?”如果没心思扯,我就直接说“岳阳”。这时就不再问了,因为九年义务教育的语文教材中有《岳阳楼记》。倘若闲得无聊呢,我就会反问一下:“汨罗江知道不?”有的知道,但仍旧有的不知道。最后只能抬出屈原的名头了:“就是屈原投江的那个地方。”问的人才终于恍然大悟。地以人名,没办法。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出名的人,出去了都不好意思介绍自己。所以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抢“孙悟空故里”“潘金莲故里”。外人看着觉得可笑,只有我知道,父母官是在为老百姓的面子操心哪。想一想,你出去介绍自己的籍贯,人家要百度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而如果有名人呢,就可以自豪地说“赵公明的出生地就是我们村里”,或者“太上老君曾经在我家对门山上升天”,或者说“日耳曼人从我们那里起源”,不仅脸上有光,而且简明扼要,省了很多口水。扯远了,打住。多年前,我跟一个哥们介绍屈原投江的地方时,他不屑一顾地说:“原来是被流放的地方啊。”他说的没错。现在的汨罗,京广铁路、武广高铁、京港澳高速、许广高速、国道纵贯南北,距黄花机场80公里。坐高铁到长沙,只要十多分钟,交通已经非常便利了。但在两千年之前,确实是一个蛮荒之地。楚王看不惯的人物,就往这边送。《芈月传》中,孙俪在剧中思念汨罗江,这是小说家言。楚国的都城迁过来迁过去,始终没有到过湖南,更不用说汨罗了。当然,话又说回来,若是当时不偏不穷,屈大夫又怎么会被流放过来呢?屈大夫不来,汨罗现在可能仍旧寂寂无闻。十九岁之前,我没有离开汨罗,但足迹不出汨罗西北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写是汨罗方言,但属于汨罗南部,有的相通,有的也有差别。从我家桃林亦仁村出发,西到洞庭湖,北往汨罗江,都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小时候,每过完春节,父亲就会和村里人一起到湖区打藜蒿。不是自己吃,而是卖了换钱。藜蒿炒腊肉,是赣菜名品,入选过北京奥运菜单主菜名单。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知道这个名字,没有见过实物。汨罗其他地方我不清楚,但我所在的村子,方圆二十里或者三十里,都没有包粽子的习俗。原因其实很简单,离湖区尚有一段距离,没有芦苇;丘陵一带,也不产箬叶。没有包装材料,自然无法做成产品。糯米稻倒是有,但因为产量比粳稻低得多,在追求温饱的年代,不会家家都种植。种植的人家,大概也只占整个耕地的十分之一左右。糯米不用来包粽子,而是磨成粉,红白喜事时做糖油粑粑。无论你信或者不信,我在十九岁之前,确实没有吃过粽子。后来出去,别人知道我是汨罗的之后,就会说:你们那里产粽子啊。我只好回答:可能吧。要说特产,长乐甜酒勉强算一个。但我们小的时候,要吃甜酒都是自己做,没有人会花钱去买。汨罗红薯粉,最近这几年在长沙饭店的菜单上也时常出现。制作这种粉的红薯,是白心的,淀粉很足,我们叫“粉皮”。生吃时口感较硬,也不甜。但做成红薯粉,品质一流。手工的粉,粗细不均,又比机器压制出来的好吃。汨罗江北,都是泥土覆盖的丘陵。我小时见过的石头,只有坟前的墓碑。当地人口中的山,其实就是一片树林,或者是没法种庄稼的荒地。山上的野果子不多,但也有一些,比如秋天的菝葜。这是一种百合科灌木,青的时候很涩,霜过后变红,味道稍甜,但也没好到哪里去。一串一串,有点像南天竹。菝葜 栎树结的果子,像锥栗,但饱含鞣花单宁,味道艰涩,让人根本不愿意把它当野果。江西人用来做豆腐,贵州人用来做粉丝,在我老家,都是在山上任其自开自落。橡栎南酸枣,薄薄的一层皮,里面一个很大的核,中间一层软滑滑的东西,被小孩子形象地称为“鼻涕果”。也只有小孩子捡了当玩具一样地尝一下,到了长沙,才发现别人是加工当零食卖的。苦槠的果子,也有点像栎子,不过要短一点。这是一种高大大乔木,每个村都有几棵。90年代初,铁山渠道还在使用。沿着往上游走,边上有一片苦槠林。每年秋收,小孩子们就成群结队去摘或者捡。树太高,只有一两个男孩能爬上去。掉下来的果实,都是被虫蛀空了。苦槠生吃的时候,没有糟蹋这个名,是真苦,水煮一下,味道才会好一些。苦槠 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种甜槠,嫩叶子掐下来晒干,可以当茶喝。再早一点,中秋节前后,就是满山的毛栗。毛栗比板栗小很多,是一种灌木。这种野果子,倒是还比较好吃。生吃是甜的,煮熟了吃,就很糯。这种植物,也主要在与岳阳县交界处的山中。当地人其实不叫“岳阳”,而是称“巴陵”。巴陵的小毛孩,都有点古惑仔的感觉,经常打群架。我小时候住外婆家,经过铁山渠道去大明街买东西,都有点怕。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就从树林里跳出几个小青年,把钱给抢走了。老实说,山上几乎没有什么好吃的野果子,端午节前后的茅莓算一种。枝条上带着刺,牵着藤,开着紫色的小花,田埂上,山坡上,菜地边,随处可见。果子酸甜酸甜,在没有零食的年代,这是最能刺激小孩子味觉的小野果。但自然界中几乎找不到一颗完整的果子,不论什么时候去找,要么就趴着一条虫子,要么就爬着几只蚂蚁。好在小孩子都不在乎,连地上的牛粪都能捡起来放嘴里的,小小的昆虫,无论成虫还是幼虫,都无关紧要。茅莓 鲁迅笔下的“覆盆子”,也就是树莓,结果的时间比茅莓早,也很常见,但小孩子不太爱摘了吃。现在市场上都有卖的了,一盒一盒装好,盖着保鲜膜,价格比车厘子还贵。水里的,可吃的野生植物,有菱角和芡实。汨罗的菱角,没有江南的味道。从来没有美女摇着船,在河中间一边捞一边唱歌。捞菱角的,都是十岁八岁的男孩子,拿一根竹竿,前端一个钩子,往水中一送,哗啦啦一大把,拖到岸边来。随便摘几颗,剥开放嘴里,突然没兴趣了,又全部哗啦啦扔水里去。芡实是学名,当地人叫鸡头米。以前,家门口池塘里每年都生。叶子、花苞、茎和果皮都长满刺,果实可磨成粉,开水冲熟,可以给小孩子当辅食,权当奶粉了。我的一对双胞胎堂弟,小时候就吃了几年的芡实粉。不知何故,现在这些年,再也没有在池塘中看到过它的踪迹。芡实 野生的荸荠,插秧的时候可以偶尔在水田中找到。叶子像灯芯草,拔起来,一颗黄豆大的小果子就被带出来。就着田里的水洗一下,放嘴里一咬,呸,一股腐烂的稻草味。大概也真的是没有什么物产,所以也不怎么会吃。满村子里找去,找遍整个村子,也没有几个会把菜做得好吃的主妇主夫。但汨罗人好客,只要来了客人,哪怕是一两个,桌上也都要摆十个八个菜,看起来是很丰盛。猪肉,一大坨一大坨,讲究一点的,放点葱;鱼肉,一大坨一大坨,讲究一点的,放点蒜;鸡肉,一大坨一大坨,讲究一点的,放点姜……菜苔,剥皮去筋,放辣椒炒;土豆,不剥皮不去筋,放辣椒炒;豆角,去筋不剥皮,放辣椒炒;冬瓜,剥皮不去筋,放辣椒炒……因此,你看着是满桌的菜,实际上就只吃到了两个味道:一个是油味,一个是辣味。汨罗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面积少。每人可能也就二十平方米。但是土地肥沃,雨水充足,不用怎么干活都能有口饭吃,人也就没有什么斗志。近年出去的人,做物流的多,但凡挣了点钱,就赶紧回来建房子。马路两旁的房子是真气派。两三百平米的别墅,在村民们口中的传说,都能花上五六百万。只是房子建好之后,就几乎没人住。再过几年,门前长树,屋顶长草。人终究是饮食动物,没有好吃的,再好的房子也留不住人。就此打住,不写了,再写,我以前的老师和同学可能要打我了。注:本文图片全部来源于网络。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miluozx.com/mlsxw/5471.html |
时间:2020/10/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医院与常青护理院签约建立ldq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