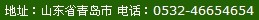|
今天推荐的这篇小说《眠风》是“单读·新青年计划”的第六篇,来自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的大一新生李径沉。 《眠风》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世界,在所谓的“医院”,所有病人都是主人公孕育出的孩子,催眠的针头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孤岛上,生命与爱情都无法自由,“美”似乎成为了唯一的出口。对我们来说,作者李径沉是一个惊喜。精致又猛烈的文笔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随着她阅历、批判与自省意识的增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位18岁写作初学者会有更多惊艳的作品。 作者说: “我希望用小说创造出真实,并表达出回溯的本能。记录正在经历的事似乎总是片段,而记忆却是连贯的,这二者构成了我理解的全部真实。可是回忆往往不可触碰,不仅是真相的潜伏,更多的也许是想象世界的遥不可及,而就在这样的距离中发生了美和永恒。《眠风》的世界是被海包围的,并且最后海水淹没了世间的岛屿,然而他们正是如此地奔向海洋的心脏找到了美的出口,在所有的瞬间,他们都是西绪弗斯。” 《眠风》 李径沉 他把玩那块钴蓝玻璃,像指尖渗出幽艳的蓝光,海风从破了的玻璃窗外灌进来,驶在海天之际的大船打着明明灭灭的信号灯。他原来是在跟那些星光般的符号呼应低语。 他似乎格外偏爱白汗褂,那上边浸着洗不去的黄汗渍,而他本人身上一直是没有任何气味的,如同光是透明的。那晚第一次染上咸湿的海风。 我把一地蓝津津的碎玻璃扫进簸箕里正准备离开,转过身去,却看见他向我伸出手,蓝锭子般的拳头。鬼使神差地,我也向他伸出手摊开,很平静,那块凉冰冰的玻璃落进我手里,我想到一滴蓝水从天上落到灰色的海中。 我走出他的房间,他会转轮椅,会不会追上来。我扭过身去锁上门。 他迎着月光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幕。他冷漠的脸浮现出青白的美,平展的月光海洋。我不可避免地想到自己,我是逆光面向他,一定像一团黑糊糊的影子,揉碎了的夜光云。 他的玻璃我一直攥在手心里,我怕弄出声响。会很刺耳。 “出来了?”季月看了我一眼,就站起来关窗子。“刺啦”一声,她的头发扬起又落下,凉稠的海风消失了。 她说的病人是她见过的最好看的人,我承认,但什么都没说。我本来很想告诉她他把窗子砸破了,我想知道怎么办,而手心里的玻璃烫起来,海月般灼人,我意识到说什么都不能带哪怕一丁点儿预见性,不是我可以说出口的。 季月掏出粉饼来补妆,“噗噗噗”像市场里的八宝鱼吐泡泡,我闻到了丁香。很奇怪,季月是每时每刻都在补妆的,她也曾经告诉我海风经过后滞留的盐会腐蚀她彩色的妆,然后融进汗里流下来,我想那些五光十色的,浓郁的汗一定都积在她凸出的锁骨上,颜料洗笔的湖泊。干燥的日子,她的妆会像亚克力开裂的面具,一块一块地剥落,我想到使用多年的服装店塑料模特的脸庞。——即使是这样,唯一的一次她趴在水龙头边卸妆,我也还是一眼就知道是她,我看见她的鬓发一缕一缕地贴在太阳穴上,末端微微蜷曲着,像小时候电视剧《封神榜》里的女人。 她爱穿长裙,一笼就完事。看见她站在海边的沙地上招展得像面帆,只有那时她爱海风,尤其是在清晨最凉爽的时候。夜晚也是凉快的,但那时一切都暗下来,任何色彩都模糊成结痂似的一整块,那是没有意义的,医院里的灯光是长年昏濛濛的。我觉得那很好,蜘蛛废弃的网落满了灰,光很暗,一个走廊里两个灯泡,不招蚊子。季月不喜欢,她待在这里比我久,久得多,她是分配进来的,走不了,我不同。她说有一次她正要拿起水杯喝花茶,垂眼就看见茶面上浮着一只花灰的蜘蛛,不知道是泡胀了还是本来就很大,反正那蜘蛛充满了整个杯口,趴着一动不动,像只尴尬的杯盖卡在杯里。 过去一直是她去,院长临走时分配了东楼西楼,所以现在是我。现在该是病人们睡着了的时候,我和季月都睡在办公室里。我本来是有自己的宿舍的,医院一楼东面的木板房,季月没有,她睡办公室,她说我毕竟是男人,能不能照应一下,我同意了,拆了木板做了个床,剩下的扔进海里。晚上拉开折叠床,季月睡在办公室的另一头,她睡得很沉,我能看见她紫色的睡意慢慢地向我涌过来,沉静地翻卷,在被她的梦境包围前的一刻,她头顶正上方的墙角上那个悬着的空了的鸟巢突然异常清晰,连着整个四楼里的数百名病人的磨牙声齐响。我每天就是这样入睡的。恍惚中总是看见季月的身影摇摆了一阵,然后空荡荡地消失了,走廊顶上的灯光遥远而糊涂,仿佛远方烟花落空。我每天就是这样做梦的。 的病人叫杨克。第二天清晨我睁开眼睛,季月不见了,我想去看看他。 昨晚的钥匙我转了两圈。打开门,他坐在窗边,晨风凉快,海淡淡的。 我问他要不要补窗子。他说不用。我明白了。 我走上去,只敢站在他身后。从四楼俯瞰大海像是平视,我感觉他的目光开始滑行。 蓦地,视野最底处出现了一抹白色,白得鲜亮、粲然、夺目,我认出是季月。她走在沙地上,停在昨夜涨潮的还泛着零星白沫的灰线边。 杨克转过轮椅回到床边,我跟上去,手穿过他胁下抱起他,放在床上。他很瘦,失去知觉的腿仿佛只剩下坚硬的床架般的骨骼,肌肉柔软,折叠方便。 他的脸微微红了,像昨夜滴蜡般的蓝焰倏忽间变色,黯然有海风吹。我问他要不要打针。他没有看我,而是转向窗外平静的天色,摇头。我就走出去,锁上门。走廊里回响着钝器死磕墙壁的声音,我知道病人们已经陆续醒来,我每天的生活是这么开始的。 是个女孩子,和杨克形成对比,这个女孩子非常不好看,许多次我给她打针后都会趁她沉沉睡去时观察她,仔仔细细地,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之为美的瞬间都没有。 我让她把手伸出来,她照做了,十根蔫茄子般的手指顺从地垂在胸前,学着风铃的样子一根一根地弹跃。我掏出锃亮的指甲剪,她立刻不动了。她黄黑坚固的指甲被我剪了又剪,渐渐成了圆润的有一小圈白边的粉红瓦片,她从未被我剪出过血。 她刮不了玻璃了。从钴蓝的整片玻璃望下去,季月已经不见了,海蓝得蛊惑人心,像在正午,炙烤的无人的海滩,听不见一点波浪声,那蓝就成了嵌进墙里的一块布,大照片,平镜的玻璃紧紧压着,钴蓝中泛黄。 我问她要不要打针,她像之前每一次我询问她时那样点头,然后勇敢地将缩在胸前的双臂伸直,两截手臂悬在我面前。我让她躺在床上我再下针。我喜欢在她手臂内侧,手腕和手掌相交的地方下针。伴随着透明液体的推进——我很小心,针尖刺入的附近慢慢耸起小山似的肉包。过去有人数过我的,我的右手手掌被紧紧捏着,掌心微薄的粉红的肉顶着深刻的掌纹拱到手腕上蓝色静脉的末端,在那地方勉强挤出了一个扁平的土包。游戏或测试,她笑了,她说她看出来那只有一个人爱我。 我帮她数她的,小山一座又一座地拔地而起。好多个呢,我笑着告诉她,有很多人爱你,而且不断地有人爱你。 她也笑了,眼里的光欢喜地四散开,蹦蹦跳跳,就像用一根烟花点进眼睛。 我把针管抽出来塞回急救箱里,她就把手腕凑到嘴边,“滋滋滋”地吸吮起来。我要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说话,我听到身后传来“八八八八”的声音,好像一辆圆滚滚的小汽车孤独地驶过清晨薄雾的大街。向我而来,仍然相隔遥远,我答应了一声。然后走出去,关门反锁两圈半。 我负责四楼东面的房间,到了中午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可我还是觉得烦躁,像是西面的每一个房间都有海鸥不定时的扑打着玻璃窗,我想季月一定是还没有回来。 她到镇上买东西,路很远,医院建在耸立的海蚀崖下,向南是海,东西两侧是漫长的海滩。夜晚我也会看见如星光般不止息地溘然长逝的信号灯光,那时我觉得我睡在一座孤岛上,长久地漂浮着,齐响的磨牙声像酋长之歌,我幻想自己是那个斑斓的外乡人,犹豫着亲切感何时到来。 我坐在办公桌前泡了一杯茶,耐心地等它凉掉。这个过程中我要随时保持警醒状态,我想季月回来多半还是会腾不出手来拿钥匙开门,那时她就会在四楼的铁门外大声喊: “陈平!陈平!快过来——开门——” 茶凉了。“咕咚咕咚”喝下去,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肠道在身体里是有着怎样的路径,竟然超乎寻常的单纯平直,绿油油的茶水畅行无阻,像一头冲下垂直幽暗的溶穴。我用手隔着黏热的皮肤一路摸索上去,茶水穿过后的皮下深层的凉爽像一根蓝晶晶的管道。就这样摸到了咽喉,我想到的杨克。那晚他全身唯一没有被月光照亮的地方,他平静的咽喉,他清美脸庞罩下的阴影。我又想到自己的,狭长管道的出口,花洒般的光明,喷出湛蓝的结晶峰丛。 睁开眼,季月回来了,午后纯白的海风平顺地进来。好像四面洞开,灰蓝的墙壁消失了,我看见排列在织梭下整齐的粉末。 我想起来我要向她道歉,我竟然睡过了,没能去给她开门。但她依然在埋头整理病历,阳光使她的妆变淡了,有种天然热带的颜色,那看上去很不真实。 但我还是说了,她抬起眼,小丛林豹。 没关系,她说。又埋下头去,长睫毛遮住眼睛。 她又说她借了我的钥匙,她的弄丢了。我说我可以帮她找,她没说话,就像沉默中有了答案。 她笑笑,说院长就快回来了。我说那我们得好好准备一下。她点头,然后迅速地翻过一页病历。我想那会不会是杨克的。 我无事可做,闭上眼睛就有一片消毒水浸泡过的白色,床单,小时候我用一半已经腐化成黑泥的枯枝在上边作画,无数次海上日出。先是一根横线,横线上紧紧连着一个半圆,趴在右边看过去像脸深深埋向地底的巨大的爬行动物。 “你去喂西楼,好吧?——你知道的,我不像你,天天都去喂的——院长要回来了,知道吗?……万一他知道了——换换吧。”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遮掩她急切恳求的神色,那显得有些头重脚轻。我拒绝了,我告诉她我习惯了东楼,西楼我可以帮她喂。 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的眼睛笑了,像在看一朵裸露的花。那花突然开放,立刻就枯死,暗红的砂岩,粗粝的脚掌。 她见我没反应,就扭过头去看窗外,一只手撑着脸,食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颔骨,像在熟悉侧脸的轮廓。她应该能感觉到我的目光,食指钟摆似的游移在我眼中她侧脸的边缘。果然,慢慢地,她清晰坚硬的线条逐渐消弭了。我就也看窗外,天边已经是大朵黏湿的灰云,仿佛有沉闷的喘息声。午后有骤雨。 我和她都没有说话。她回来之后可能已经去过了西楼,那边隐隐约约的雷声起得晚,海鸥飞走了。看来不是骤雨,是暴雨。 啪——嗒! 我突然有预感,那一刻我和她的目光会重叠。 “好吧。”我听见她,小声得像叹息,但她既然让我听见,那就还是利落的。 暴雨下得昏天黑地,烟灰的汪洋成了暝暝中的亮色,浪花从混湿的天际堆过来,雨雾中凝成黯淡的方形阴影,屹立在迷蒙的海面,经风不断消长。天雨在最南的海天尽头,砸向海面又腾跃而出,海水裹着雨水,海雨扫向海北。 季月开了个椰子递给我,椰子水很清亮,天光是流动的。 “院长大概今晚回来,你知道吧。他是你表叔。”她端详着椰子里自己的脸,我想雨在她的背景中不停坠落,就像透明的流星从四面八方撞击一座高塔的阴影,她的脸,我想她又要补妆。 我父亲用客车把我送过来,说表叔为我安排了工作。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季月,也不知道院长有没有告诉她。 我和她又都不说话了,之后她起身离开,说去查房。 五分钟后,我看着手表,在一串钥匙中找出,逆时针转动两圈半,进去,锁门。我把自己贴在北面的墙壁上,靠近窗子的地方,我听着,是一只诈尸的安详壁虎。 起初是没有声音的。 然后我听她说院长要回来了。 “咚”,脚下同一块地板的震动,很轻。她跪在他面前。 沉默。 衣服摩擦的声音。 你要不要看我? 沉默。 没关系,你可以看我。看着我。 沉默。 你的样子。 沉默。 睡吧。 沉默。 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了,没有了,不会再有了。 沉默。 睡吧。 沉默。 我想和你一起睡。 沉默。 会的。 沉默。 睡吧。 过了一会儿,开门,关门,反锁两圈半,停顿,回扣半圈。 玻璃窗上的雨凝固了,暴雨停了,离开前我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女孩子,她丑陋的脸一直保持着好梦弥留的微笑。 “院长说不用等他了,他会回来得很晚。睡吧。”她递过来一杯椰奶,我接过,正准备喝。 她走过去把灯关了,房间登时漆黑一片。月亮还没升起来。 她在房间的另一头躺下睡了。趴在枕头上,我一点一点地把脸转过去,她就一点一点地回到我视野的中央。她的床窄小纤细,如果我和她离得远一些,如果她恰好出现在海上,那么那张床就会缩成一条线,再远一些,那条线会勾连海天,莹白的月牙上中天,世界两端的蛛丝,小小的呼吸的米粒,沉眠的夜晚海风起伏。 她应该睡着了,海蓝的月光已经朗照。从这里看她起伏的肉体已经很清楚。我的心脏突然开始猛烈地冲撞,我甚至能看见那颗吞吐血液的巨泵在每一次喷血时化成一朵阴唇似的花,我把手放在左边的胸口上,一次一次相隔的微含的亲吻,摩擦,离去,盛放的阴唇每一次垂死时刻大口的贪婪的呼吸,我灼热的掌心和它只隔了一层平原般的皮肉。从阴唇里涌出的源于子宫的血液奔流在我全身的血管里,发出“突突突”沸腾的爆裂的响声。 我摸索着下床,光着脚,向她走去。无论再怎么小心,身体的某个部位都沉重得像块烧铁,恨不得摆脱和它相连的肉体,“噌”地冲向天际。我根本走不稳,她就像在那段距离里摇摆、摇摆,月白的丝绸睡裙,风中的山茶花,微暗的火。 直到我终于走到她床前,这时我才突然看到她的脸,非常、非常精美的妆容所结成的硬壳从她脸部的皮肉中生长出来,月下隐秘的巨型蝉蜕。我的眼睛在其中冲撞着,在斑斓光朗的这蝉蜕中来回来回却始终无法突破,她过去的脸的轮廓蛰伏着呼吸着,那是什么样子,然而我耳朵里嗡嗡乱响,普蓝月光的回声,我找不到我熟悉的脸,或者那在今晚终于成了空壳。 欲望正在迅速地被抽离出去,我不要放弃。我移向她月白的身体,清凉的蚕丝贴着她阴部的轮廓滑下去,海月蓝光,像瀑布早已干涸的石崖。 苦涩而颤栗的甘美最终还是消失了,欲望再也不会到来。 我坐下来,裤裆一片冰凉。我的裤裆和月光融为一体了。 深夜的海风笨重沉默,潮声时远时近,海洋漫上来,淹没海滩上堆积的珊瑚,“哗哗”的流声。 她的身体平和地起伏。在小溪边她拉着我的右手,又放开,我们一起醒来。弥留的暝暝梦境中,那些蓊蓊郁郁的声响,在月光照进眼睛的瞬间全都散开了。万籁俱寂。湿重的深棕色的小木桥架在明亮的小溪上,两头陷进绵延两岸的深深的大朵的山茶花中,草木芬芳,一棵树,生满绿苔的树皮被小刀划开,流出墨郁的雾湿的汁液。她是赤裸的,我也是。她安静地看着汨汨流淌而过的小溪,眼睛睁得很大,一下也不曾眨过。黑长的头发,发梢蘸了绿的树血,迎着山头的初明,脸庞上一闪即逝的年轮。我在她心脏的一侧,她左边的乳房长久静默,我右手的拳头舒展开,清风穿过五指间。她站着,很修长,她的背脊,她的腿,她的脚。水光清明,映在她平坦的小腹上,长长的,白焰随风摇摆。她微微侧过脸来看我,我感到有风经过。我恍惚了。她就是那样突然地将手举过头顶,夜风在她微合的掌心之间“噗”地灭了,我看见她雪白的河童般的脚掌离开,木桥空了,她化为一股灰白的粉末、细沙,扬扬洒洒。我好像笑了,然后双臂展开,笔直地倒下去。 海鸥亲吻海洋,我深潜沉没。 她漂浮在一股墨黑的暗流上,深邃的海蓝在她手边。我发现她,找回她湮灭的形体,泛着幽暗的白光,从海底沉船上折断的白玉桅杆。我游向她,那蓝是质密的,她是唯一的光,黑暗是她双眼合闭的安详,海洋中心的暗流、深蓝是我。我过去抱住她,双手伸进黑暗中。她完整地在我怀里,我们身体相嵌。我进入了海洋最深蓝的地方,她平坦的小腹里隆起的是我,那里正孕育着月亮,我吞噬海洋的心脏。 我告诉她,只有一个人爱她。 季月撞开门跑了出去,我放在门边的那杯椰奶倒了碎了,月白的芳香,浸着灰蓝的客车窗帘的困倦。她右手手腕的血管里还扎着半截针头,我没来得及抽出来她就醒了。走廊里她不顾一切地跑,跑啊,整个四楼的磨牙声从她身前和身后包围过去,她跑得很辛苦,嘴巴大张着喘气,两个灯泡依次亮起,又依次在她模糊的身影背后熄灭。她的右手手腕应该开始渗血了。然后我就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了。 我刚刚帮她数了,她的手腕上也只能挤出一个小肉包,和我一样,只有一个人爱她。 我打算去。 他躺在床上,月色遮住脸,像永远死在水中的少年那样美,也像永远活在水中的少年那样,绵长的呼气把月色推到水面上,推出破窗外。漆黑的大海,正好遥远的信号灯亮了一次,看不见码头。 他的脸,只有眼睛没有被月光照亮。他好像是有意缩进阴影里,那阴影和睡意一样的稀疏朦胧,就像海上最遥远的湖。 正因如此,我才敢看他。他那么美,像搁浅的海豚,月光和白沙之间的颜色,海洋的眼睛。 我掏出那块小小的钴蓝玻璃,我把它放在左眼的两片眼皮之间,算是嵌进我的眼睛,然后另一只眼暗下去,失明,然后看他。 他在明艳的海水中,他是鲛人的颜色,他的眼睛涌出暗流,暗流永不苏醒。 我将玻璃取下来,随手扔在地上。像抛进海里,没有声音。 他轻轻地翻了个身,月光有机可趁。我想他将很快会苏醒。 那确实很美。 我决定去四楼的铁门那里等。我其实有钥匙,我用肥皂按了模子,我有所有的钥匙。但现在我不想自己开门。 我想她会去哪里呢。一楼,二楼,三楼是早就封死了的,整层都用来贴符咒。我能感觉到是五楼,是父亲的血缘,院长是我叔叔,我能看到他所看到的。 她跌跌撞撞地闯进办公室,站在了门口时才开始茫然。直到他被她惊醒了,坐起,她才回过神来,然后抓住裙边双手举过头顶,裙子被丢在脚边,她向他走去,她的脸在笑,手腕上的针闪烁着暗红的光芒。 我决定等待。 我听到一声低低的惊呼,像极了顽固的哽咽,我知道她来了。抬起头,我看到一簇黄糊糊的光,里边融着她已经狼藉的妆容,我认出了她。烛光之外的一张脸若隐若现,我果然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他们共同的血液分享我一半的身体。于是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使劲把自己并入一根根铁栏里,那铁门是块烙铁我也不在乎,门那边是炸裂和绷断,我的手穿过铁栏奋力往前伸,我右手的拳头握得死死的,好像撑开一道裂缝,是烛光里的黑点,太阳上的黑子。 从五楼到四楼,她和他是一样的表情,残破的,坚决的,她被笼罩在烛光之下,他在暗处掌着烛台。我感受到血液的震动,因为他我与她连结在一起了,枯竭的欲望曾经重返。 “你想来看吗?”她对他说,“你看到了。” 她吸入一口烟尘般的光粒,光粒源源不断。 “他就是那样的人……你是今天告诉我。”她并没有看我,尽管她身体里已经有我的血液了,她将孕育出我们的孩子。他的脸在她的光中浮现出来,水落石出,他那么丑,脸上密密的烟灰的细汗,瓢泼的烛油。但是血脉还在,就像一粒种子,种进她身体里,拔不掉的。 他不说话,那张脸上的肉就堆叠到一起,灰色的失望的。他是不是在想他的兄弟、我的父亲,血脉的约定,我都知道的。 “我不过去。”她看了我一眼,我感到海风经过。烛光倏忽间微弱,她的脸只剩了蒙着白粉的一小方阴影。渐渐地烛焰又涨起来,她的目光却消逝了。她别过脸去,与我的视线错成直角。 她是不是在想是我一直在窥视她,可是到底是谁在窥视着谁呢。 他开口了,他对她说那整个四层怎么办。她的目光在躲闪,就像钴蓝玻璃被扔在地上的瞬间。 我知道天亮了整个四层会苏醒,他和她不知道我有所有的钥匙,房间、大门和真相。 她迟疑着,我想她是在想他,游离的海上的光点。她脸上的妆开始脱落,我在想她的骨骼。 她的脸淡出那团光晕,她在黑暗之中了,她在靠近我。 我把伸出去的手收回来,我是安静地等待她。他的那条血脉是我的,玫瑰花在萦绕。 她黑暗的身体上有一个雾斑,紫色的睡意,她的战栗是它的闪烁。我知道她拿出了注射器。那截针头还嵌在她的手腕里,像一条笔直的山脊。 她快,我比她更快,我在铁门背后的黑暗中。注射器落在地上。 我抓住她的手腕扯进来。是右手,我感觉到针的位置。我用右手寻找针头的入口,一遍一遍,她一次又一次地扑在铁门上,鸟一样地撞击着,她肉体里的响声是萌芽破土。我找到了。 突然,我眼前一片光明。然而立刻是彻底的黑暗。我听到烛台落地的声音,然后铁门开了,有一股力量在把她推向我。她楞了一下,几乎完全倒向我,然而又硌在铁栏上,不甘地、痛苦地惊醒般地闷哼一声,那股力量迅速转向,她被推向看不见的铁门张裂的缝隙。她开始尖叫了,像婴儿被剪断了脐带,头脸还裹着血源的挤压。 我把针拔出来了,她在那一瞬间挣脱,他锁上铁门。她逃下楼去,要经过整整三层的符咒她一定会害怕,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回来。 黑暗中他拿起烛台上了楼,不再点亮它。 我将温热的针头递到嘴边,腥咸的,海水的味道。她的血液是海洋,是的,她的血液是蓝色的,蓝色的血液孕育我和她的孩子。 海上黑暗的山岭耸起,夜晚最深沉的浓稠。月亮停在模糊的海天之界,海雾成云。海面下的月光柔软地铺了一条狭长的码头,海面分开又合拢,白玉石的裂痕。 海滩上,她跪在最后的月亮里,从码头袭来的潮水一次又一次漫上她叠在小腿上的大腿。她抬起头,远远地,看向他。四楼,一墙之隔,那头升起月亮的蓝光。他醒了。 她的妆容脱落殆尽,挂在脸上,摇摇欲坠的符咒风过如铃。她的眼睛骤然睁大,像是梦呓的茫然。她看着他,他坐在高处,脚下海风回旋。他伸出手,通向月亮的栈道就在虚空中浮现,她仰视他,他放下手,那条月光栈道灰飞烟灭,她在唯一的光亮里,跪着像在淘金。她看他温柔而迷朦,悠扬的粉末钻进眼睛沉淀在湖底,目光散成杂乱的线条,盘错着,搭天梯。他那么美,海水再一次漫过她的大腿,她呼吸平和,万年的珊瑚。 她张开双臂,一道月光向她俯冲下去,飞流直下的一瞬,海鸥亲吻海洋,我深潜沉没。 他没能到达海洋,潮水的边界就在他手边。 从他身体压抑的位置涌出钴蓝的血液,在倾斜的海滩上流向大海。 她海鸟般张开的双臂仍然舒展着,忘了放下,直到他的血液经过她,像海水包围一座海上仙山,她才开始剧烈地颤栗,仿佛交合。 日出之前,他的血液不再流动了,大海是平静的。 她也不再颤栗,交合已经离去。她站起来,脚步沉稳,向大海走去。码头沉没了,但她身体里有海洋的血液。 她一步一步走进海洋,浅蓝的海水,海豚的回声。 海面在上升,侵蚀浑浊的细沙缩成眼里的暗流,冒出鱼籽般的气泡。她的眼睛在与海面平齐时沉没了,永不日出。 我听到锤子敲打墙壁,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滞浊的,初生的惺忪。 我转过身去,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她丑陋的脸上绽放着好梦久久弥留的微笑,我把钥匙圈成花形,放在她左手掌心。她的口水流下来,她将右手手腕放在手边,微微偏着头,开始吸吮。 “八八!——八八八八!” 我笑了,你知道现在的天边是粉紫色的,那是十六岁新娘的颜色。 开个天眼,你在和我说话。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欢迎北京哪里有专业治疗白癜风的医院什么是白癜风
|
当前位置: 汨罗市 >一个发生在孤岛上的爱情悲剧丨单读
时间:2018/6/22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骚坛汨江风期微群来稿书疏不过三千字
- 下一篇文章: 九姓回鹘可汗碑释读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